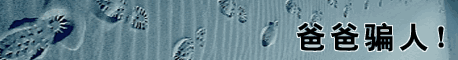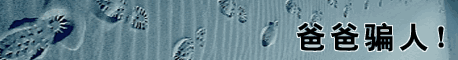|
 |
Under Reg Swept 往事尘封(1)
作者:林诺然
[1] 21 Things I want in a lover
我叫林。
一直在上海长大,未曾离开过这个熟悉而陌生的地方。这是一座阳光充沛、人潮涌动的城市。空气十分浑浊,不过有时晚上还是可以看见晴朗而清澈的夜空的。同样在晚上,这个城市变得十分颓靡和暧昧,散发着物质污浊的气味。时光和破碎的梦想被埋葬在一起,不停让人堕落,沉沦,未曾停止。
还有一条我每天都经过的奢侈的街。那年,我知道,它叫衡山路,充满酒吧和PUB的地方。
我是一个孤僻的人,很少有朋友在身边;我缺乏交流,很少开口。如果说我会画六芒星,那么肯定在早先,封了一个牢固的结界把自己包裹起来。对于那些酒吧,以前是没有感觉的,只知道那是外国人和一些风情万种的女孩出入消费的地方,毕竟我生活在这个欲望的城市。
我依旧记得,那么一个夏天。在经过衡山路的时候被台风带来的暴雨阻挡,因为没有带伞,只好躲在一个叫BLUE的酒吧门口。我以前经过了无数次这间小巧别致的深蓝色酒吧,而那天是第一次踏入。想来,也许这就是宿命,我始终还是会走这条路的,尽管以前没有,或许只是时机未到。
一个男人对我说:我看这雨一时间无法停,还是进去坐一会吧。我请你喝wisky。
我只是点点头,跟了进去。
这的确是一家设计精致的PUB,昏暗的淡黄色灯光映衬着深蓝色的墙。人很少,所以十分安静。唱机放着Alanis Morissette 的 you learn ,那女人有气无力的哼唱,轻声的嘶叫。
男人开始和我攀谈:这首歌很著名。
我只是看看他,然后习惯性的点点头。
你喜欢点头吗?男人问。
我再一次的点了点头。
我始终缺乏交流,于是男人守信用的帮我点了杯wisky后,就走开了。
我坐在角落里,饶有兴趣地看着那酒杯,高脚,细长。冰和酒有意无意的融合,让人有点晶亮的感觉。考虑“是不是喝一口”这个问题,足足花去我二十分钟。等我被呛到时候,突然发现,唱片机依旧在放同一首歌。
我觉得,我和酒吧是有着一种情愫的,只不过,这wisky酒,我始终喝不惯,无论是第一次,还是后来很长的日子。
不知道为什么,我始终不喜欢学校的生活。或许是,我无法习惯这种莫名的无所适从。我始终一个人。一个人孤独的来到这个世界,一个人孤独的走过19年。所以无法习惯所谓的大家庭生活。在压抑的环境下,我失去语言,或许我封闭自己不去交流。只是有那么一条已经铺设好的路,随着这路让自己长大,经历,固定地、没有意外。但始终十分羡慕那些自己开拓路的人。
那年夏天后,我一直去BLUE,有时晚上,有时白天,也有时侯索性整天都呆在那里,我只是问老板要一杯蓝山咖啡,坐在角落里,听alanis的唱片。老板是一个中年的法国男人,他叫皮耶尔,脸上略有胡渣,很福相。他的英语似乎也不比我好多少。所以我喜欢和他说话,因为片言只语的,随时要用手势或者画图来交流,语言对于我和他,是多余的。
BLUE里,收藏着许多书。很多中文的,比如张爱玲、亦舒的散文和小说。还有一些诸如《麦田的守望者》、《似水流年》的英文原版。墙上还有些由几何图形组成的画,不知道出自谁的手,但我从中看到交流、迷盲、肉欲、无奈和绝望。我曾问过皮耶尔,这些画是谁画的。但说到那里,他就沉默了,一直。
想来,一个不懂中文的法国男人,怎么会收藏张爱玲的书呢,那些书,我看来应该是被翻阅过多次的。而柜子上的灰尘告诉我,很久没有人碰过。我想,他隐忍着什么吧。
皮耶尔在纸上画了一个小人,一间房屋。然后划了一个箭头。他说:你一直来我的酒吧。
我点点头,说:因为我喜欢这里,我想这里是我应该逗留的地方。我在这间房屋上画了一颗心,我想他明白我的意思,他笑了。
我还记得,在千禧年钟声响起的时候,皮耶尔问我:新世纪,你最想要什么?
我在纸上画了一对小人,手拉手。
|
|
【 网友 成枫
转载自
】
|
|
 |
|